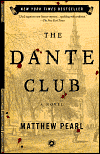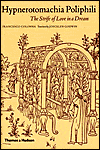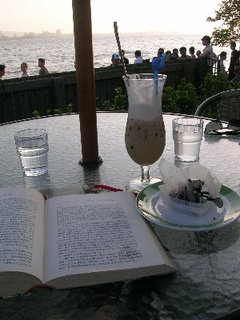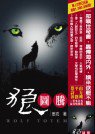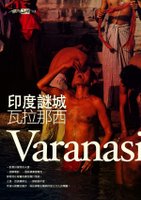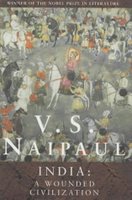因為工作關係到了康乃狄克州兩星期。週末的時候不想與大伙兒到紐約,於是開了四小時車到美國文化發源地、一度被譽為美洲大陸的「雅典」的波士頓。
波士頓最為人所知的,是她孕育了美國的獨立革命。將英國茶葉全倒進海裏,把英國人激怒的,正是波士頓人;首次與英軍對壘的,也是波士頓人。
然而,波士頓之所以成為革命的起點,有賴當地商人如約翰.漢考克 (John Hancock) 的財源滾滾、政治家如山姆.亞當斯 (Samuel Adam) 的雄辯滔滔、以及雲集當地的文學家、哲學家等的前衛思想;班傑明.富蘭克林 (Benjamin Franklin) 便是其中之一。最早在這裏定居的清教徒,主要是為了不滿英國教會的腐敗;之後他們提倡了解放盲目的宗教信仰、解放英國統治、以及解放黑奴。波士頓因而被認為是「自由之子」的誕生地。
是故,波士頓的主要名勝是一條貫穿全市的「自由小徑」(Freedom Trail),在地上用紅磚指引。經過的全是二百多年前與革命有關的教堂、會堂、墳場、戰場、以及
一艘戰艦與
一位名人的故居。那艘戰艦,乃是美國最著名的戰艦,三十多戰未嚐敗績,名為「美國憲法號」(USS Constitution),暱稱「老鋼鐵號」(Old Ironside);那位名人,曾單騎匹馬,半晚突破重重崗哨,預警英軍的進攻:他便是保羅.李維爾 (Paul Revere)。
葛拉威爾 (Malcolm Gladwell) 在其《引爆趨勢》(The Tipping Point; Gladwell, 2002) 裏亦多次引用李維爾的故事。然而,李維爾之所以著名,全靠一位詩人幫他賣廣告。
那位詩人名叫亨利‧沃茲沃恩‧朗費羅 (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),乃是第一個斐聲國際的美國詩人。李維爾便全因他寫的「李維爾午夜快騎」(The Midnight Ride of Paul Revere) 一詩而名垂千古。
至於建於 1795 年、多次面臨被拆毀的命運的「美國憲法號」,亦全因另一位詩人奧利佛‧溫德爾‧侯姆斯 (Oliver Wendell Holmes) 所寫的「老鋼鐵號」(Old Ironside) 而得以保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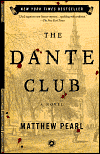
這兩位著名詩人,加上詹姆斯‧拉塞爾‧婁維爾 (James Russell Lowell) 等,被稱為「紳士派詩人」(The Brahmin Poets) 或「爐邊詩人」(Fireside Poets)。
然而,我之所以提到他們,主要是因為他們是第一批將但丁《神曲》從意大利文翻譯成英文的美國人,並將《神曲》引進美國。他們便是美國但丁學會 (The Dante Society of America) 的前身,名為「但丁會」(The Dante Club)。
說到這裏,相信很多朋友已經知道我繞了這麼大個圈子而準備寫的,是以「但丁會」為名的懸疑小說:《但丁俱樂部》(The Dante Club; Pearl, 2004)。

但丁 (Dante Alighieri),與莎士比亞、歌德並稱世界三大文學巨匠。儘管他如此著名,很多朋友,甚至我美國的同事,都沒有聽說過。他寫的《神曲》(意:La Divina Commedia;英:The Divine Comedy),將死後的世界描述成「地獄 (Inferno)」、「煉獄 (Purgatorio)」、與「天堂 (Paradiso)」。人在地獄裏受到與其罪相稱的懲罰:以牙還牙,以眼還眼。但丁則稱這概念為「Contrapassio」。是的,有點像龍豹別墅的地獄模型,極度血腥殘忍。
「煉獄」這個概念,一直在羅馬天主教會裏流傳至今。「煉獄」裏的靈魂,罪不至受永火之苦;他們的罪是
愛的罪,愛了不應該愛的東西或人,還是可以用火來煉淨。煉淨後便能回到天堂。時至今日,每年十一月,仍是天主教會的「煉靈月」,教友為「煉獄」的亡魂祈禱,望他們早升天國。
但丁寫「煉獄」(1308-21),比教會正式將其納入教義 (Council of Ferrara-Florence, 1438?) 還早了百多年。但丁本身卻是因為天主教會的迫害而流亡,至死未能回到佛羅倫斯 (Florence),他的故鄉。
朋友,如果你還是覺得但丁很陌生,那讓我再告訴你甚麼人在「煉獄」裏受苦。「煉獄」分七層,裏面的人分別犯了:驕傲 (Pride)、嫉妒 (Envy)、忿怒 (Wrath)、懶惰 (Sloth)、貪婪 (Greed,或 Avarice & Prodigality)、貪饕 (Gluttony)、與迷色 (Lust) 等七種罪。很熟悉了吧?對,它們便是天主教教義裏的七罪宗,或電影《七宗罪》的主題,或我甚喜愛的《鋼之鍊金術師》的人造人的名字。與它們相對應的懲罰,便是由但丁判決的。
且說回《但丁俱樂部》。由於丹‧布朗 (Dan Brown) 的《達文西密碼》(Brown, 2003) 賣到洛陽紙貴,出版社便乘勝出版了另外兩本以兇案、文學、以及歷史古蹟貫穿全書的懸疑小說。他們便是《四的法則》(Caldwell & Thomason, 2004) 與《但丁俱樂部》(Pearl, 2004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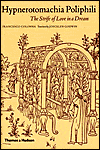
丹‧布朗最為人詬病的,是其語文水準,以及抄襲《聖血.聖杯》(Baigent, Lincoln, & Leigh, 1983)。說到底,他只是一名中學教師。於是出版社找來出自名校普林斯頓大學與哈佛大學的作家,以文藝復興時的艱澀鉅著《尋愛綺夢》(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; Colonna, 2003) 及中世紀的但丁《神曲》(Alighieri, 1988) 為骨幹,出版了《四的法則》與《但丁俱樂部》兩部小說。

這次水準明顯提高了。出版社竟敢將《四的法則》與符號學家安伯托‧艾可 (Umberto Eco) 的《傳科擺》(Foucault’s Pendulum; Eco, 1989) 相提並論!而《但丁俱樂部》的作者馬修.珀爾 (Matthew Pearl) 則是哈佛文學系與耶魯法律系畢業,整部《但丁俱樂部》都在模仿十九世紀中用的英語。出版社以為這次定必更成功。

事實卻證明,叫好的東西未必叫座,叫座的亦未必叫好。這兩部小說都沒有做成什麼熱潮。其實震撼如《聖血.聖杯》、深奧如《傳科擺》,都從沒真正暢銷。丹‧布朗的成功,正正是因為其通俗易懂!我認識的美國人,連但丁都沒聽說過;七罪宗只能叫他們想起畢彼特,那又怎會買《但丁俱樂部》呢?
別以為我愛扮高深,這些小說我雖然全看過,但是老實說,如果想拿一本上飛機消閒,還是看丹‧布朗最醒神吧.
Reference:Alighieri, D. (1988). The Divine Comedy. (D. L. Sayers, Trans.). Penguin. Retrieved from
http://search.barnesandnoble.com/booksearch/isbnInquiry.asp?EAN=9780140440065Baigent, M., Lincoln, H., & Leigh, R. (1983). Holy Blood, Holy Grail. Dell. Retrieved from
http://search.barnesandnoble.com/booksearch/isbnInquiry.asp?EAN=9780440136484Brown, D. (2003). The Da Vinci Code. Doubleday. Retrieved from
http://search.barnesandnoble.com/booksearch/isbnInquiry.asp?ISBN=0385504209Caldwell, I. & Thomason, D. (2004). The Rule of Four. Dell. Retrieve from
http://search.barnesandnoble.com/booksearch/isbnInquiry.asp?EAN=9780385337113Colonna, F. (2003). Hypnerotomachia Poliphili: The Strife Of Love In A Dream. (J. Godwin, Trans.). Thames & Hudson. Retrieved from
http://search.barnesandnoble.com/booksearch/isbnInquiry.asp?EAN=9780500511046Eco, U. (1989). Foucault's Pendulum. (W. Weaver, Trans.). Harcourt. Retrieved from
http://search.barnesandnoble.com/booksearch/isbnInquiry.asp?EAN=9780151327652 (曾被譽為每位知識份子都應該有一本放在桌面的小說。)
Gladwell, M. (2002). The Tipping Point: How Little Things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. Little, Brown & Company. Retrieved from
http://search.barnesandnoble.com/booksearch/isbnInquiry.asp?EAN=9780316346627Pearl, M. (2004). The Dante Club. Random House. Retrieved from
http://search.barnesandnoble.com/booksearch/isbnInquiry.asp?EAN=9780812971040
 這個故事,便是 Bernard Cornwell 為建於五千年前的史前巨石陣 (Stonehenge) 所設想的原因。既謂「史前」,就是未有歷史、未有文字的時候,亦因而沒有資料解釋我們新石器時代的祖先為什麼要大費周章,從西南威爾斯 (Wales) 運送巨石到 Salisbury 平原上,興建一座天文台一樣的龐然大物。有多大?其中有些石頭足四個人高、七隻象重!
這個故事,便是 Bernard Cornwell 為建於五千年前的史前巨石陣 (Stonehenge) 所設想的原因。既謂「史前」,就是未有歷史、未有文字的時候,亦因而沒有資料解釋我們新石器時代的祖先為什麼要大費周章,從西南威爾斯 (Wales) 運送巨石到 Salisbury 平原上,興建一座天文台一樣的龐然大物。有多大?其中有些石頭足四個人高、七隻象重!






.jpg)
.jpg)





.jpg)

.jpg)